- 發布時間:2019-12-25 15:17:03 瀏覽次數:3378
- 說戰國文字“再”、“兩”的字形結構
-
(彰化師大國文系)
(首發)
清華九《治政之道》簡21-22整理者釋文作「皮(彼) (一)而【二一】不巳(已),亓(其)
(一)而【二一】不巳(已),亓(其) (二)乃巳(已),厽(三)而不巳(已),四
(二)乃巳(已),厽(三)而不巳(已),四 (鄰)之者(諸)侯乃必不
(鄰)之者(諸)侯乃必不 (諒)亓(其)悳(德)以自固于我。」並注釋指出:已,停止。一而不已,其二乃已,三而不己云云,指為不道一而再,再而三。諒,信也。自固于我,大意是與我的友好關係更加堅固。文意與《孟子‧公孫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相類。[1]其中讀為「二」的「
(諒)亓(其)悳(德)以自固于我。」並注釋指出:已,停止。一而不已,其二乃已,三而不己云云,指為不道一而再,再而三。諒,信也。自固于我,大意是與我的友好關係更加堅固。文意與《孟子‧公孫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相類。[1]其中讀為「二」的「 」字形作
」字形作 ,王寧先生指出:「
,王寧先生指出:「 疑讀為再,字從二會意,?聲。」[2]
疑讀為再,字從二會意,?聲。」[2]
謹按:王氏之說可從, 字當分析為從「二」,「?」聲。《廣雅‧釋詁四》:「再,二也。」《玉篇》:「再,兩也。」王筠《說文句讀》:「再者,兩也。」[3]《上博四‧簡大王泊旱》13「君王毋敢
字當分析為從「二」,「?」聲。《廣雅‧釋詁四》:「再,二也。」《玉篇》:「再,兩也。」王筠《說文句讀》:「再者,兩也。」[3]《上博四‧簡大王泊旱》13「君王毋敢 (戴)害【13】
(戴)害【13】 (蓋)」,「
(蓋)」,「 」字過去釋為「哉」,分析為「口」寫作「二」形。[4]現在看來顯然應釋為「再」,可能是「再」的專用字。「再」常與「載/戴」相通。《詩‧秦風‧小戎》:「載寢載興。」載,韓《詩》作「再」;曹植〈應詔〉詩,《文選》李善注引作「再」。《呂氏春秋‧順民》:「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楊樹達云:「『載』讀為『再』,音同通用。」[5]《清華一‧金縢》簡2:「秉璧
」字過去釋為「哉」,分析為「口」寫作「二」形。[4]現在看來顯然應釋為「再」,可能是「再」的專用字。「再」常與「載/戴」相通。《詩‧秦風‧小戎》:「載寢載興。」載,韓《詩》作「再」;曹植〈應詔〉詩,《文選》李善注引作「再」。《呂氏春秋‧順民》:「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楊樹達云:「『載』讀為『再』,音同通用。」[5]《清華一‧金縢》簡2:「秉璧 (戴)珪」,今本作“植璧秉珪”,陳劍先生指出“簡文‘秉璧戴珪’,傳本及諸引文雖有‘戴’字作‘載’、‘植’等之不同,但其後皆爲‘璧’,而圭則皆言‘秉’。聯繫習見的‘加璧’,頗疑《金縢》之文很可能本來就是作‘戴璧秉珪’的。”[6]《易林·中孚》:「武王不豫,周公禱謝,載璧秉圭,安寧如故。」又《需之无妄》:「載璧秉珪,請命于河;周公尅敏,冲人瘳愈。」《同人之晉》、《離之否》同。段玉裁曰:「載、戴古通用也。」《詩•周頌•絲衣》:「絲衣其紑,載弁俅俅。」 鄭玄箋:「載猶戴也。」那麼「再」之於「載」,猶「再」之於「戴」。
(戴)珪」,今本作“植璧秉珪”,陳劍先生指出“簡文‘秉璧戴珪’,傳本及諸引文雖有‘戴’字作‘載’、‘植’等之不同,但其後皆爲‘璧’,而圭則皆言‘秉’。聯繫習見的‘加璧’,頗疑《金縢》之文很可能本來就是作‘戴璧秉珪’的。”[6]《易林·中孚》:「武王不豫,周公禱謝,載璧秉圭,安寧如故。」又《需之无妄》:「載璧秉珪,請命于河;周公尅敏,冲人瘳愈。」《同人之晉》、《離之否》同。段玉裁曰:「載、戴古通用也。」《詩•周頌•絲衣》:「絲衣其紑,載弁俅俅。」 鄭玄箋:「載猶戴也。」那麼「再」之於「載」,猶「再」之於「戴」。
程鵬萬先生根據射壺銘文「再」寫作 (壺甲蓋銘),指出此字右部所從就是兩個
(壺甲蓋銘),指出此字右部所從就是兩個 ,這種字形應該就是“再”字原始的寫法,後來為了書寫的方便,將其中的一個偏旁用重文符號“=”替代,遂變成
,這種字形應該就是“再”字原始的寫法,後來為了書寫的方便,將其中的一個偏旁用重文符號“=”替代,遂變成 ,如果“=”拉長就會變成
,如果“=”拉長就會變成 。射壶
。射壶 字所從“再”(精母之部)是聲符的話,
字所從“再”(精母之部)是聲符的話, 大概與平夜君鼎銘“載鼎”之“載”(精母之部)相通。平夜君鼎銘“載鼎”之“載”,學者認為可以讀為精母之部的“
大概與平夜君鼎銘“載鼎”之“載”(精母之部)相通。平夜君鼎銘“載鼎”之“載”,學者認為可以讀為精母之部的“ ”。《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 ,設飪也。從丮、食會意,才聲,讀若載。”[7]程先生所說大致可從,不過對於戰國文字的「再」寫作
,設飪也。從丮、食會意,才聲,讀若載。”[7]程先生所說大致可從,不過對於戰國文字的「再」寫作 郭店楚墓竹簡·語叢49
郭店楚墓竹簡·語叢49 郭店楚墓竹簡·窮達以時15
郭店楚墓竹簡·窮達以時15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昔者君老1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昔者君老1
 羌鐘
羌鐘 陳章壺等等,筆者傾向於其下的「二」可能已經被重新分析為數字「二」,也就是「
陳章壺等等,筆者傾向於其下的「二」可能已經被重新分析為數字「二」,也就是「 」的「二」旁,[8]而非省簡符號。
」的「二」旁,[8]而非省簡符號。
前面提到《玉篇》:「再,兩也。」王筠《說文句讀》:「再者,兩也。」那麼「兩」的字形跟「二」是否有關呢?答案是肯定的。金文「㒳/兩」作 (4179,小臣守簋)、
(4179,小臣守簋)、 (4141,圅皇父簋)。[9]陳夢家先生指出金文“兩”字係兩個相並立的“丙”。[10]李建平、 龍仕平先生曾列出如下字形:
(4141,圅皇父簋)。[9]陳夢家先生指出金文“兩”字係兩個相並立的“丙”。[10]李建平、 龍仕平先生曾列出如下字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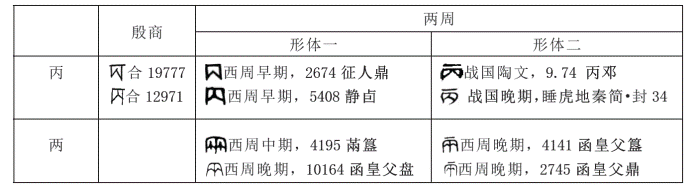
並指出:「可見無論是形體一還是形體二,“兩”都是兩個並立的“丙”字。」其說與陳夢家相同,並可從。[11]于省吾先生認為:「兩」象縛雙軶於衡,引申之凡成對並列之物均可稱「兩」。[12]吳振武、黃天樹、李建平、 龍仕平等先生贊同這個意見。[13] 若依照葛亮先生的研究,「丙」是「房俎」之「房」的初文,[14]那麼「兩」可分析為兩個並立的「房俎」。究竟何說為是,還需要進一步的討論。
春秋、戰國文字的「兩」多作 ,[15]目前所見楚簡也幾乎寫作這樣的形體,如
,[15]目前所見楚簡也幾乎寫作這樣的形體,如 成人25。但是「兩」為何從二「丙」形演變從「羊」形,一直以來都不清楚,往往以「字形訛變」帶過。
成人25。但是「兩」為何從二「丙」形演變從「羊」形,一直以來都不清楚,往往以「字形訛變」帶過。
值得注意的是,清華九《禱辭》17「兩」作 ,在字形下方加上義符「二」,結構與「再」相同,只要「二」跟「
,在字形下方加上義符「二」,結構與「再」相同,只要「二」跟「 」中間的筆畫穿插在一起之後看起來便像是「羊」了。這樣我們才明白「兩」、「再」的字形是有關的,也呼應了《玉篇》:「再,兩也。」的說法。
」中間的筆畫穿插在一起之後看起來便像是「羊」了。這樣我們才明白「兩」、「再」的字形是有關的,也呼應了《玉篇》:「再,兩也。」的說法。
附記:本文承蒙鄔可晶先生審閱指正,筆者十分感謝!
[1] 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中西書局2019年11月,頁138注80。
[2] 王寧:《讀清華簡〈治政之道〉散札》,復旦網,2019.11.28,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490。
[3] 宗福邦等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7),頁201。
[4] 拙著:《楚文字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2011.12)頁342、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一~八)》(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12月),頁432。
[5] 楊樹達:《讀呂氏春秋札記》,載《楊樹達文集16•積微居讀書記》頁212。
[6] 陳劍:《清華簡〈金縢〉研讀三題》,《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1-163頁。
[7] 程鵬萬:《東周“再”字探源》,第八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國際論壇,中興大學歷史系主辦,2019年8月15-16日。
[8] 關於「重新分析」的例證,還可參見陳劍:《說“規”等字並論一些特別的形聲字意符》,《源遠流長:漢字國際學術研討會暨AEARU第三屆漢字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9] 參見《金文編》,頁547。
[10]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頁94。
[11] 李建平、 龍仕平;《量詞“丙”“兩”的語源及其歷時演變》,《古漢語研究》2018年3期,頁33。另參見劉釗:《“小臣墻刻辭”新釋》〉復旦網,2009.01.02、王子楊:《甲骨文所謂的「內」當釋作「丙」》,《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三輯,頁233。
[12] 于省吾:《釋兩》,《古文字研究》第10輯。
[13] 吳振武:《讀侯馬盟書文字札記》,中國語文研究(香港)第6期,1984、黃天樹:《黃天樹骨文論集》,頁344、。
[14] 葛亮:《古文字“丙”與古器物“房”》,第二屆古文字學青年論壇,2016年,中研院史語所。
[15] 參見吳振武:《讀侯馬盟書文字札記》,中國語文研究(香港)第6期,1984、《古文字詁林》頁5153。
(编者按:本文收稿时间为2019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