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布時間:2024-09-20 15:50:22 瀏覽次數:1502
- 丁家嘴簡樂器名札記(四則)
-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首發)近日,由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博物館、老河口市博物館、武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編著的《湖北出土楚簡五種》出版,該書公布了五地七座楚墓出土的共計八百余枚楚簡,使我們有幸得以閱讀、學習這些珍貴的戰國楚文字資料。[1]
五種楚簡中的丁家嘴楚簡2009年出土於武漢市江夏區丁家嘴一、二號墓,其內容包含卜筮禱祠記録和遣册兩種。丁家嘴二號墓遣册8號簡記載多種樂器及附件,是繼信陽楚簡“樂人之器”簡後,又一集中記載多種樂器及附件的戰國遣册簡,對研究戰國時期楚樂器的稱名、組合等有重要價值。此簡簡文所涉樂器,如鼓、鼙、瑟,又見於信陽簡及其他楚簡文獻中,可以確釋,還有一些以往未見的樂器(或附件)之名尚需進一步討論。初讀之後,我們對這些樂器名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寫在這裡,請方家指正。爲便於討論,先依據整理報告並結合本文觀點,將丁家嘴樂器簡簡文列出:
一□ ,一鼓,一〖
,一鼓,一〖 (鼙)〗,二
(鼙)〗,二

 之
之 。一耑(短)
。一耑(短) (瑟),一埶(篞),一
(瑟),一埶(篞),一 (笙),一篸(參)
(笙),一篸(參) (差)。二〼(丁家嘴2-08)
(差)。二〼(丁家嘴2-08)
信陽簡“樂人之器”與本簡關係密切,在此一併列出:
樂人之器:一 (肆)坐脠(延)鐘,少(小)大十又三,柅條,厀(漆)劃(畫),金
(肆)坐脠(延)鐘,少(小)大十又三,柅條,厀(漆)劃(畫),金 (珥)。一
(珥)。一 (肆)坐(座)〖脠(延)磬〗,少(小)大十又九,柅條,厀(漆)劃,緄維。二
(肆)坐(座)〖脠(延)磬〗,少(小)大十又九,柅條,厀(漆)劃,緄維。二 瑟,一壴瑟。一壴竺(筑)。二笙,一
瑟,一壴瑟。一壴竺(筑)。二笙,一 竽,皆又(有)
竽,皆又(有) (韜)。一〖彫(雕)〗鼓。一彫(雕)
(韜)。一〖彫(雕)〗鼓。一彫(雕) (鼙)。二㯱(枹)。四㯮(㭬)。一烕(滅)盟(明)之柜(虡),躔土螻,厀(漆)青黄之劃(畫)。三漆
(鼙)。二㯱(枹)。四㯮(㭬)。一烕(滅)盟(明)之柜(虡),躔土螻,厀(漆)青黄之劃(畫)。三漆 (瑟)桊(梡)。一壴
(瑟)桊(梡)。一壴 (翇),一
(翇),一 (翇)。(信陽2-18+3)[2]一、
(翇)。(信陽2-18+3)[2]一、
“ ”字,整理報告釋爲“
”字,整理報告釋爲“ (椎)”,認爲其似指鼓槌。該字字形寫作:
(椎)”,認爲其似指鼓槌。該字字形寫作:
 丁家嘴2-08
丁家嘴2-08
諦審圖版,此字當隸定爲“ ”,其字右所从的“
”,其字右所从的“ ”即“鳧”。“
”即“鳧”。“ ”“
”“ ”楚文字多見,依據“勹”旁寫法的不同,其字形大致可分爲四種:
”楚文字多見,依據“勹”旁寫法的不同,其字形大致可分爲四種:
A: (
( )鐘离公
)鐘离公 鼓座,《集成》429
鼓座,《集成》429
B: (
( )包山183
)包山183 (
( )清華十一.五紀106
)清華十一.五紀106  (
( )清華一.尹至05
)清華一.尹至05
C:
 (
( )曾侯乙46、89
)曾侯乙46、89  (
( )包山258
)包山258  (
( )望山2-13
)望山2-13 (摹)
(摹)
D:

 (
( )清華十三.參不韋019、091、100
)清華十三.參不韋019、091、100
四種寫法中:A類“ ”所从的“勹”旁大致寫作匍匐人形,基本保留了早期文字中“勹”的象形寫法;B類所从的“勹”旁是由A類訛變形成,寫作“九”形;[3]D類所从的“勹”旁新見,寫作“
”所从的“勹”旁大致寫作匍匐人形,基本保留了早期文字中“勹”的象形寫法;B類所从的“勹”旁是由A類訛變形成,寫作“九”形;[3]D類所从的“勹”旁新見,寫作“ ”形,也是由A類訛變形成。[4]C類“
”形,也是由A類訛變形成。[4]C類“ ”“
”“ ”所从的“勹”旁比較特殊,它雖基本保留了“勹”的人形,但“勹”旁的左側筆畫與“隹”的豎筆形成共筆。李家浩先生最早對這類寫法作出分析,認爲前舉包山258號簡之“
”所从的“勹”旁比較特殊,它雖基本保留了“勹”的人形,但“勹”旁的左側筆畫與“隹”的豎筆形成共筆。李家浩先生最早對這類寫法作出分析,認爲前舉包山258號簡之“ (
( )”字寫作从“艸”从“隹”从“
)”字寫作从“艸”从“隹”从“ ”,並謂:“‘
”,並謂:“‘ ’的左側一畫與‘隹’的左側一豎公用,右側一畫的中間加有一點。這種筆畫公用和加點的情況,在戰國文字中常見。金文‘鳧’所从‘鳥’旁作‘隹’。於此可见,簡文此字應該釋爲‘
’的左側一畫與‘隹’的左側一豎公用,右側一畫的中間加有一點。這種筆畫公用和加點的情況,在戰國文字中常見。金文‘鳧’所从‘鳥’旁作‘隹’。於此可见,簡文此字應該釋爲‘ ’。”[5]《説文》謂“鳧”“从鳥
’。”[5]《説文》謂“鳧”“从鳥 聲”,于省吾先生指出所謂“
聲”,于省吾先生指出所謂“ ”旁當是“勹”旁。[6]因此包山簡之字確切地説應是“隹”“勹”共筆。[7]C類中曾侯乙46、89號簡及望山2-13號簡之字,李家浩先生指出它們爲一字之異,[8]單育辰先生將兩字正確改釋爲“
”旁當是“勹”旁。[6]因此包山簡之字確切地説應是“隹”“勹”共筆。[7]C類中曾侯乙46、89號簡及望山2-13號簡之字,李家浩先生指出它們爲一字之異,[8]單育辰先生將兩字正確改釋爲“ ”“
”“ ”(即“鳧”),不過單先生認爲望山簡之字應嚴格隸定爲“
”(即“鳧”),不過單先生認爲望山簡之字應嚴格隸定爲“ ”,“土”上所从爲“
”,“土”上所从爲“ ”之省聲。[9]後出《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公布了相關簡文更加清晰的紅外照片,結合這些新圖版,可知曾侯乙簡的“
”之省聲。[9]後出《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公布了相關簡文更加清晰的紅外照片,結合這些新圖版,可知曾侯乙簡的“ ”、望山簡的“
”、望山簡的“ ”亦存在“隹”“勹”共筆的情況,而望山簡的“
”亦存在“隹”“勹”共筆的情況,而望山簡的“ ”字中“勹”旁又與“土”旁共筆。[10]丁家嘴簡8中的“
”字中“勹”旁又與“土”旁共筆。[10]丁家嘴簡8中的“ ”字,其“
”字,其“ ”旁可歸爲C類,而其“勹”與“土”旁共筆的寫法,則與望山簡之字相同。
”旁可歸爲C類,而其“勹”與“土”旁共筆的寫法,則與望山簡之字相同。
“ (鳧)”从“勹”聲,若依整理報告認爲其指鼓槌,則“
(鳧)”从“勹”聲,若依整理報告認爲其指鼓槌,則“ ”可讀爲訓鼓槌的“枹”。《説文》:“枹,擊鼓杖也。从木包聲。”“包”即从“勹”聲。[11]“枹”訓鼓槌古書常見,如《左傳》成公二年:“左并轡,右援枹而鼓。”《楚辭·九歌·東皇太一》:“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楚辭·九歌·國殤》:“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前舉信陽遣册簡“樂人之器”之“㯱”,劉信芳先生將其讀爲擊鼓杖之“枹”。[12]又馬王堆M3遣册簡9:“建鼓一,羽旌
”可讀爲訓鼓槌的“枹”。《説文》:“枹,擊鼓杖也。从木包聲。”“包”即从“勹”聲。[11]“枹”訓鼓槌古書常見,如《左傳》成公二年:“左并轡,右援枹而鼓。”《楚辭·九歌·東皇太一》:“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楚辭·九歌·國殤》:“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前舉信陽遣册簡“樂人之器”之“㯱”,劉信芳先生將其讀爲擊鼓杖之“枹”。[12]又馬王堆M3遣册簡9:“建鼓一,羽旌 (飾);卑(鼙)二。鼓者二人,操枹。”[13]此二處“枹”即緊接在鼓、鼙之後記録,與丁家嘴簡的“
(飾);卑(鼙)二。鼓者二人,操枹。”[13]此二處“枹”即緊接在鼓、鼙之後記録,與丁家嘴簡的“ (枹)”記載的位置一致。戰國楚墓出土鼓槌多見,如湖北江陵望山M1、天星觀M1、包山M1、藤店M1、棗陽九連墩M2等,[14]或成對出土,[15]可資參考。
(枹)”記載的位置一致。戰國楚墓出土鼓槌多見,如湖北江陵望山M1、天星觀M1、包山M1、藤店M1、棗陽九連墩M2等,[14]或成對出土,[15]可資參考。

望山M1:B1-2、3(2件) 天星觀M1(2件) 

包山M1:44-1 九連墩M2:351-2、3(2件) 表一:楚墓出土的鼓槌
“
 ”又可考慮讀爲“柎”,訓鼓座。古音“勹”在幫紐幽部,“付”屬幫紐侯部 ,音近可通。[16]包山遣册簡258及簽牌“鳧茈”之“鳧”分别寫作“
”又可考慮讀爲“柎”,訓鼓座。古音“勹”在幫紐幽部,“付”屬幫紐侯部 ,音近可通。[16]包山遣册簡258及簽牌“鳧茈”之“鳧”分别寫作“ ”“
”“ ”(包山258、簽牌52),即是其例。[17]“柎”指器物的底座,典籍“柎”或作“跗”。《説文》:“柎,闌足也。”段玉裁注:“柎、跗正俗字也,凡器之足皆曰柎。”“柎”亦訓鼓座。《左傳》宣公四年:“伯棼射王,汏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孔穎達正義云:“車上不得置簨簴以懸鼓,故爲作跗,若殷之楹鼓也。”楊伯峻注:“鼓跗猶今之鼓架。”[18]又《説文》:“
”(包山258、簽牌52),即是其例。[17]“柎”指器物的底座,典籍“柎”或作“跗”。《説文》:“柎,闌足也。”段玉裁注:“柎、跗正俗字也,凡器之足皆曰柎。”“柎”亦訓鼓座。《左傳》宣公四年:“伯棼射王,汏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孔穎達正義云:“車上不得置簨簴以懸鼓,故爲作跗,若殷之楹鼓也。”楊伯峻注:“鼓跗猶今之鼓架。”[18]又《説文》:“ (虡),鐘鼓之柎也。”尹灣漢墓《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記有“鼓柎”“鼙柎”,如“乘輿鼓柎五十六”“鼓柎百廿”“鼙柎卌四”(YM6D6正)。[19]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出土有建鼓座,自名“
(虡),鐘鼓之柎也。”尹灣漢墓《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記有“鼓柎”“鼙柎”,如“乘輿鼓柎五十六”“鼓柎百廿”“鼙柎卌四”(YM6D6正)。[19]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出土有建鼓座,自名“ 鼓”,“
鼓”,“ ”即丁家嘴簡“
”即丁家嘴簡“ ”字所从。范常喜先生指出其當讀爲“跗鼓”,謂“鼓座銘文中的自名‘鳧(跗)鼓’即裝有跗足的鼓,這與文獻中所記‘足鼓’之名也正相吻合”。[20]
”字所从。范常喜先生指出其當讀爲“跗鼓”,謂“鼓座銘文中的自名‘鳧(跗)鼓’即裝有跗足的鼓,這與文獻中所記‘足鼓’之名也正相吻合”。[20]
丁家嘴簡記載的器物“ (柎)”位於鼓、鼙之後,讀爲鼓座之“柎”大體與信陽“樂人之器”先記鼓、後記鼓架的記録順序相符。不過,丁家嘴簡記鼓、鼙各一,整理者已指出二者分别對應墓中出土的一件虎座鳥架鼓和一件漆木鼓。若將簡文斷讀爲“二
(柎)”位於鼓、鼙之後,讀爲鼓座之“柎”大體與信陽“樂人之器”先記鼓、後記鼓架的記録順序相符。不過,丁家嘴簡記鼓、鼙各一,整理者已指出二者分别對應墓中出土的一件虎座鳥架鼓和一件漆木鼓。若將簡文斷讀爲“二

 之
之 (柎)”,則“
(柎)”,則“ (柎)”有兩件,鼓、鼙有别,鼓柎大概不宜一并記録,懷疑這裡的簡文當斷讀爲“二
(柎)”有兩件,鼓、鼙有别,鼓柎大概不宜一并記録,懷疑這裡的簡文當斷讀爲“二 ,
,
 之
之 (柎)”,若此則“二
(柎)”,若此則“二 ”有可能指鼓枹。
二、埶(篞)
”有可能指鼓枹。
二、埶(篞)
簡文“埶”,整理報告認爲其應是某種樂器,大致可信。依據簡文記録樂器的順序,“埶”有兩種釋讀方向:一是與瑟同爲絲類弦樂器或作爲瑟的附屬物;二是與笙、參差(簫)同爲匏竹類管樂(與笙、參差相關的討論參看本文三、四條)。
淅川和尚嶺春秋晚期二號楚墓出土一件“銅鎮墓獸座”,該器自名“且埶”。[21]“埶”“爾”音近,又典籍“柅”“檷”通用,劉國勝先生據這件“銅鎮墓獸座”指出楚遣册簡中的“柅”當指墓中所出的“彩繪雙角器”及鐘架、磬架的立柱。有關鐘架、磬架的立柱,劉先生指出:
信陽遣册2-018號簡與2-03號簡是前後相連的兩簡,記録“樂人之器”。“柅”分别出現在記編鐘、編磬的內容中,皆作:柅條,漆畫。對這句簡文,也有不同釋法。但一般都認為這是針對鐘、磬架的記録,當可信。如果我們釋柅不誤的話,“柅”就是指鐘、磬架的立柱。信陽1、2號墓出土的鐘架、磬架的立柱都是帶足柎的,形制與上述“彩繪雙角器”的立柱及“鎮墓獸座”相仿。“柅條”的“條”可能就指鐘、磬架的橫樑。[22]
然依據對丁家嘴簡中的“埶”所處位置的分析,若將簡文“埶”同“銅鎮墓獸座”的自名及楚遣册簡中的“柅”聯繫起來,恐怕只能將“埶”理解爲瑟座。我們知道,目前所見楚遣册簡中的瑟座稱“龹/桊”,[23]故將“埶”理解爲與器座有關之物似不甚合適。又信陽簡“樂人之器”瑟後記“竺(筑)”,古音“筑”在端紐覺部,“埶”在疑紐月部,[24]將“埶”讀“筑”似亦不可通。
簡文“埶”或可讀爲“篞”。 《說文》:“涅,……从水从土,日聲。”“埶”“日” 古音相近,南越王墓車馹虎節銘文作“王命命車 ”,李家浩先生指出“
”,李家浩先生指出“ ”从“埶”省聲,當讀爲“馹”,[25]是其例。“篞”是古代管樂器名。《爾雅·釋樂》:“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郝懿行義疏:“謂之簥者,《御覽》五百八十引舍人曰:‘大管聲高大,故曰簥。簥者,高也。中者聲精密,故曰篞。篞,密也。小者聲音清妙也。’”“篞”與笙、參差皆爲匏竹類管樂,符合遣册按類别記録樂器的邏輯。
三、
”从“埶”省聲,當讀爲“馹”,[25]是其例。“篞”是古代管樂器名。《爾雅·釋樂》:“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郝懿行義疏:“謂之簥者,《御覽》五百八十引舍人曰:‘大管聲高大,故曰簥。簥者,高也。中者聲精密,故曰篞。篞,密也。小者聲音清妙也。’”“篞”與笙、參差皆爲匏竹類管樂,符合遣册按類别記録樂器的邏輯。
三、 (笙)
(笙)
簡文“ ”,整理報告隸定爲“
”,整理報告隸定爲“ ”,讀爲“笙”,觀點可信。此字寫作:
”,讀爲“笙”,觀點可信。此字寫作:
 丁家嘴2-08
丁家嘴2-08
細審圖版,可知此字字左當爲“龠”,楚文字“龠”旁寫如:
龢: 王孫遺者鐘
王孫遺者鐘

 鐘
鐘
 (竽):
(竽):
 鐘
鐘  (管):
(管): 清華八.虞夏01[26]
清華八.虞夏01[26]
丁家嘴簡文左半雖漫漶,但對比可知當爲“龠”旁無疑。故簡文可隸定爲“ ”,分析爲从“龠”“生”聲,與从“竹”之“笙”爲一字之異。“龠”“竹”皆與竹管(或以竹管爲部分結構的)樂器有關,《説文》謂“龠,樂之竹管”,“竹”則表示這類樂器的材質。在表示竹管樂器的字中,“龠”“竹”皆可作表意偏旁,相關字例多見於楚文字。如前舉
”,分析爲从“龠”“生”聲,與从“竹”之“笙”爲一字之異。“龠”“竹”皆與竹管(或以竹管爲部分結構的)樂器有關,《説文》謂“龠,樂之竹管”,“竹”則表示這類樂器的材質。在表示竹管樂器的字中,“龠”“竹”皆可作表意偏旁,相關字例多見於楚文字。如前舉 鐘之“
鐘之“ ”字,張亞初先生指出“
”字,張亞初先生指出“ 爲竽之本字。龠爲義符,于爲其聲。
爲竽之本字。龠爲義符,于爲其聲。 字本義是樂器”。[27]又李家浩先生補充:“‘篪’字異體作‘䶵’,从‘龠’从‘虒’聲。‘
字本義是樂器”。[27]又李家浩先生補充:“‘篪’字異體作‘䶵’,从‘龠’从‘虒’聲。‘ ’與‘䶵’的結構相同。‘
’與‘䶵’的結構相同。‘ ’與‘竽’的關係,猶‘䶵’與‘篪’的關係。”[28]清華八《虞夏殷周之治》之字,整理報告指出其从“龠”“龹”聲,是“
’與‘竽’的關係,猶‘䶵’與‘篪’的關係。”[28]清華八《虞夏殷周之治》之字,整理報告指出其从“龠”“龹”聲,是“ 管”之“管”的專字。[29]簡文“
管”之“管”的專字。[29]簡文“ ”與“笙”的關係可資類比。“笙”寫作“
”與“笙”的關係可資類比。“笙”寫作“ ”首次見於楚文字中,楚遣策簡雖未見“
”首次見於楚文字中,楚遣策簡雖未見“ ”字,但有“笙”字,見於前舉信陽簡“樂人之器”中,可資比較。
四、篸(參)
”字,但有“笙”字,見於前舉信陽簡“樂人之器”中,可資比較。
四、篸(參) (差)
(差)
簡文“篸 ”,整理報告謂:
”,整理報告謂:
《説文》竹部“篸,差也,從竹參聲”,段玉裁將“差也”改作“篸差也”,并云:“《集韻》:‘篸差,竹皃。初簪切。’又‘篸,竹長皃。疏簪切。’按:木部“槮,木長皃。”引“槮差䓷菜”,蓋物有長有短,則參差不齊,竹、木皆然。”“ ”字下部所從即《古文四聲韻》卷三“徙”字的古文寫法。“徙”與“斯”古音極近,而古書中“虒”與“斯”可通用。疑簡文“簁”當讀爲“篪”,是一種竹管樂器。
”字下部所從即《古文四聲韻》卷三“徙”字的古文寫法。“徙”與“斯”古音極近,而古書中“虒”與“斯”可通用。疑簡文“簁”當讀爲“篪”,是一種竹管樂器。
“篸 ”位於笙之後,將其歸爲吹奏管樂很有道理,我們認爲這裡的“
”位於笙之後,將其歸爲吹奏管樂很有道理,我們認爲這裡的“ ”不必破讀爲“篪”,“篸
”不必破讀爲“篪”,“篸 ”可讀爲“參差”或“篸
”可讀爲“參差”或“篸 ”,指簫。整理報告已指出,“
”,指簫。整理報告已指出,“ ”所从之“
”所从之“ ”即“徙”字的古文寫法,“
”即“徙”字的古文寫法,“ ”在楚文字中又多用爲“長沙”之“沙”,[30]上古音“
”在楚文字中又多用爲“長沙”之“沙”,[30]上古音“ (徙)”屬心紐支部,“沙”屬山紐歌部,“差”屬初紐歌部,[31]“
(徙)”屬心紐支部,“沙”屬山紐歌部,“差”屬初紐歌部,[31]“ ”“差”可通。楚地出土文獻中“
”“差”可通。楚地出土文獻中“ ”(或从“
”(或从“ ”之字)與“差”亦見互通,如郭店簡《五行》簡17“
”之字)與“差”亦見互通,如郭店簡《五行》簡17“ (差)沱(池)其
(差)沱(池)其 (羽)”,[32]安大簡《詩經·關雎》“晶(參)
(羽)”,[32]安大簡《詩經·關雎》“晶(參) (差)苀(荇)菜”(“
(差)苀(荇)菜”(“ ”或作“
”或作“ ”),[33]皆是其例。
”),[33]皆是其例。
“參差”一詞如整理報告所引,本訓不齊貌,如《詩·周南·關雎》:“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傳世文獻中“參差”作爲樂器簫之名見於《楚辭》。《楚辭·九歌·湘君》:“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王逸《楚辭章句》:“參差,洞簫也。言己供脩祭祀,曕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誠欲樂君,當復誰思念也?”[34]或謂“參差”又作“篸 ”。洪興祖補注:“《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參差,不齊之皃。……此言因吹簫而思舜也。《洞簫賦》云:‘吹參差而入道德。’洞簫,簫之無底者。篸
”。洪興祖補注:“《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參差,不齊之皃。……此言因吹簫而思舜也。《洞簫賦》云:‘吹參差而入道德。’洞簫,簫之無底者。篸 ,竹貌。”[35]《説文》:“簫,參差管樂,象鳳之翼。从竹,肅聲。”《爾雅》“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郭璞注:“(大簫)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簫,一名籟。”[36]戰國時期的簫即排簫,[37]所謂“參差管樂,象鳳之翼”即是對其形制的形象描述。戰國楚墓出土的排簫,如曾侯乙墓、棗陽九連墩M2分别出土兩件13管排簫,可資參考。[38]同時,“參差”作爲樂器簫之名首次出現在楚簡文獻中,爲戰國樂器名物研究提供了新的認識。
,竹貌。”[35]《説文》:“簫,參差管樂,象鳳之翼。从竹,肅聲。”《爾雅》“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郭璞注:“(大簫)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簫,一名籟。”[36]戰國時期的簫即排簫,[37]所謂“參差管樂,象鳳之翼”即是對其形制的形象描述。戰國楚墓出土的排簫,如曾侯乙墓、棗陽九連墩M2分别出土兩件13管排簫,可資參考。[38]同時,“參差”作爲樂器簫之名首次出現在楚簡文獻中,爲戰國樂器名物研究提供了新的認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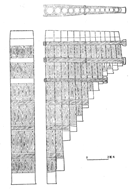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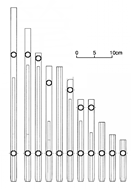

曾侯乙墓排簫(C·28、85) 九連墩M2竹排簫(M2:278) 表二:楚墓出土的排簫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李天虹主編:《湖北出土楚簡五種〔壹〕》,文物出版社2024年。荆州博物館等編,李天虹主編:《湖北出土楚簡五種〔貳〕》,文物出版社2024年。
[2] 釋文參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二)·葛陵楚墓竹簡、長臺關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48、154頁。范常喜:《信陽楚簡“樂人之器”補釋四則》,《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范常喜:《信陽楚簡“樂人之器”所記編鐘、鐘槌名新釋》,《文物》2021年第12期。范常喜:《從信陽遣策簡談“虎座鳥架鼓”鼓架的定名》,《江漢考古》2024年第1期。
[3] 參看單育辰:《談戰國文字中的“鳧”》,《簡帛》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28頁。
[4] 蔡一峰:《清華簡〈參不韋〉新見“符”字考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6期。
[5] 李家浩:《信陽楚簡中的“柿枳”》,《簡帛研究》第二輯,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12頁。
[6] 于省吾:《釋勹、 、
、 》,《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99年,第374-378頁。
》,《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99年,第374-378頁。
[7] 包山簡“ ”旁中“隹”“勹”的共筆關係不及其他“
”旁中“隹”“勹”的共筆關係不及其他“ ”旁明顯,可能是書手書寫草率、筆勢未及所致。
”旁明顯,可能是書手書寫草率、筆勢未及所致。
[8] 李家浩:《信陽楚簡“澮”字及从“龹”之字》,《中國語言學報》第1期,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89-199頁;收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9] 單育辰:《談戰國文字中的“鳧”》。
[10] 于夢欣:《〈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圖版札記二則》,《漢字漢語研究》2022年第3期。
[11]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中華書局1998年,第237 頁。
[12] 劉信芳:《楚簡器物釋名》(下),《中國文字》第廿三期,(臺北)藝文出版社1997 年,第80頁。
[13]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中華書局2014年,第228頁。
[1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91、93頁。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91、93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棗陽九連墩M2樂器清理簡報》,《中原文物》2018年第2期。
[15]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總編輯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湖北卷》,大象出版社1999 年 ,第111-127頁。
[16] 郭錫良編著:《漢字古音手册》增訂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76頁。
[17]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編著;陳偉、彭浩主編:《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六)·包山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2024年,第92、106頁。
[18]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中華書局2016,第744頁。
[19]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编:《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第105、110、111頁。
[20] 有關“ ”通讀爲“跗/柎”的討論以及典籍有關“跗/柎”訓釋,可參看范常喜先生文。范常喜:《建鼓自名“鳧(跗)鼓”考》,《古文字論壇》第三輯,中西書局2018年,第245-254頁。
”通讀爲“跗/柎”的討論以及典籍有關“跗/柎”訓釋,可參看范常喜先生文。范常喜:《建鼓自名“鳧(跗)鼓”考》,《古文字論壇》第三輯,中西書局2018年,第245-254頁。
[2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09-111頁。
[22] 劉國勝:《信陽遣册“柅”蠡測》,簡帛網2010年10月22日。
[23] 參看范常喜:《楚墓出土瑟座用途與名稱重探》。
[24] 郭錫良編著:《漢字古音手册》增訂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05、152頁。
[25] 李家浩:《南越王墓車馹虎節銘文考釋》,《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71-78頁。
[26] 李守奎編著:《楚文字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30頁。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中西書局2018年,第178頁。
[27] 張亞初:《金文新釋》,《第二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3年,第293-309頁。
[28] 李家浩:《 鐘銘文考釋》,《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4-81頁。
鐘銘文考釋》,《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4-81頁。
[29]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第162頁。
[30] 禤健聰:《戰國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研究》,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273-274頁。
[31] 郭錫良編著:《漢字古音手册》增訂本,第3、94、122頁。
[32]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荊門市博物館編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一)·郭店楚墓竹書》,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7頁。
[33] 黄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中西書局2019年,第69、70頁。
[34] [漢]王逸撰;黄靈庚點校:《楚辭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6、47頁。
[35]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卷二,中華書局2006年,第60頁。
[36]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十三經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94頁。
[37] 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71頁。
[38]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72-174頁、彩版六。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文物出版社2023年,第147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棗陽九連墩M2樂器清理簡報》。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為2024年9月20日1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