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布時間:2021-09-17 16:07:07 瀏覽次數:2434
- 讀《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伍、陸)》札記(二)
-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首發)
近日《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伍、陸)》一書出版[1],與前四冊簡對讀之後有些新的發現,在此列出以供大家討論。
(一)范初不與少、貴共盜趙壽繒案考實解書
張朝陽先生曾指出[2],五一廣場簡牘中的,簡736、簡661以及簡702屬於同一案件。《五一(伍、陸)》公佈後筆者重新對這一案件進行了梳理,發現還有兩枚簡與該案件相關,分別為簡543與簡2625+2553。因此就目前而言共有五枚簡與本案相關,這五枚簡中除702號簡形製為竹簡外,其他四枚在形製上均屬於木兩行。且這四枚簡字跡較為一致,在涉案人員上有較多的重複,當屬於涉及同一案情的四枚散簡,極有可能屬於同一封文書。四枚簡按照出版號順序羅列如下,標點為筆者所加:
置初舍籠中,十月廿五日出之市,還,不知繒五十五匹所在,詣御門亭長丁壽,告壽收毄(繋)初。少名萇不處姓。萇辤:盜十五匹,不知餘所在。疑初與萇共盜壽,書到考實姦詐,正處言,則祉543(木兩行2010CWJ1③:261-23)
貴汝何從得紙,貴曰:我於空籠中得之。初疑貴盜客物,即於壽比籠廋索,見壁後有繒物,初問貴是何等繒,貴曰不知,初曰:汝見持繒紙素言不知,即收縛貴,付661(木兩行2010CWJ1③:263-11)
卿市繒當有主名。壽墨不應,明廿七日,趙壽與未央俱去初舍,不雇初籠僦直。初謂壽、未央:卿來止出入一月不當雇樵薪直?壽曰:我亡物,非能復謝卿。壽移止曲平亭部736(木兩行2010CWJ1③:263-86)
兼左部賊捕掾則言,考男子范初
不與少、貴共盜趙壽繒,解書 詣左賊 □月□日開
2625+2553(木兩行2010CWJ1③:283-73+283-1)
從簡文內容看,簡2625+2553應當屬於該封文書的標題簡,簡文簡明扼要的敘述了該封文書屬於考實解書,考實結果為男子范初沒有與少、貴二人一同盜竊趙壽的繒。雖然簡2625+2553為標題簡,但東漢時期司法類文書的標題簡一般而言是置於文書最末尾的,可參考長沙東牌樓東漢簡《光和六年諍田自相和從書》,該封文書屬於一枚合檄簡,簡文最末尾便是該封文書的標題“監臨湘李永例督盜賊殷何言:實核大男李建與精張諍田自相和從書”。[3]既然從標題簡可知該文書屬於解書,則該封文書應當遵循的是解書的書寫格式,據溫玉冰考證“解書的文書結構大約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摘錄了上級機構要求查核案件的文書內容;第二部分則是下級官吏的調查及處理報告,包括涉案人員的身份訊息、案情以及調查結果。”[4]543號簡中有“書到,考實姦詐,正處言”,而這句話一般屬於解書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分界線,該句內容前屬於上級文書摘錄,該句之後屬於案件調查報告。由此可以判斷簡543應屬於該封解書第一部分的內容,即對上級機構要求查核案件文書的摘錄。從簡文來看,上級機構是通過御門亭長丁壽的報告得知此案件的,文中提到趙壽將繒放在初房間的籠中後,在十月二十五日外出回來後五十五匹繒就丟失了,於是將此事報告給了御門亭長丁壽,懷疑是初盜竊了他的繒,要求丁壽關押初。之後據丁壽的調查,找到了盜竊趙壽之繒的嫌疑人之一“少”又名“萇”,但“萇”只承認他盜竊了十五匹繒,其餘的不知所蹤。於是亭長丁壽將此案報告給了上級機構,上級機構懷疑“初”與“萇”一同盜竊了趙壽的繒,於是指派兼左部賊捕掾“則”對此案進行調查。
在“則”對案件進行調查之後,又發現了一名犯罪嫌疑人“貴”,簡661便涉及到貴在盜竊後是如何被初所發現的,簡文中提到初詢問貴他的紙是從哪裡得來的,貴說他在空的籠中所得,初於是懷疑貴也是盜竊趙壽繒的嫌疑人之一,於是與趙壽一同對貴所說的空籠進行搜索,發現果然有繒,於是便詢問貴,但貴卻回答他不知空籠中有繒。初對貴進行反駁後便將貴捆綁起來移送到官府。此處有個問題是,為何初見到貴持有紙便懷疑貴與趙壽繒失竊案有關。筆者認為此處的“紙”應當還是指“紙”本義,《說文》:“紙,絮一笘也”,即漂洗蠶繭時附著於筐上的絮渣,呈方形。而本案中失竊的繒則是絲織品的總稱,《急就篇》第二章:“服瑣緰㠿與繒連”顏師古註:“繒者,帛之總名,謂以絲織者也”,所以就此處而言繒與紙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
最後在這四枚簡中,簡736與其他三枚關聯程度較低,張朝陽先生曾就簡736單獨進行過討論,其認為該枚簡反應的了東漢時期的房屋租賃糾紛情況,其認為簡文中的“不雇初籠僦直”與“不當雇樵薪直”中的“籠僦直”與“樵薪直”指代的是房租。但是綜合整個案件情況來看二者似乎有別的解釋。關於“籠”這個字,張朝陽先生認為其本意似乎指某種儲物櫃,筆者認為此處的“籠”字很有可能是從其本意的,簡543開頭則提到,“置初舍籠中”,即是指趙壽將買來的繒放置在初房間的“籠”中,此處的“籠”應當與簡736“不雇初籠僦直”中的“籠”含義一致。而簡543中“舍”與“籠”同時出現,指代的是兩種含義不同的事物,“籠”應當是指初房間中的用於儲物之器。此外關於該枚簡是否反映了房屋租賃糾紛情況,筆者認為還有待商榷。首先簡736中提到“明廿七日,趙壽與未央俱去初舍”,若是趙壽與未央租賃了初舍,那他們應當租住在初舍,何談要一同去往初舍。其次在初要求趙壽交付“樵薪直”時,趙壽回答“我亡物,非能復謝卿”,“謝”字在此處可能是報答或酬謝之意,《後漢書·皇甫規傳》:“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李賢注:“謝猶酬也”。筆者推測可能是初幫忙抓住了盜竊趙壽繒的另一嫌疑人“貴”,於是趙壽需要酬謝“初”,但由於案件缺簡太多,此種說法有待進一步證實。最後張朝陽先生認為趙壽由於無錢交付初之房租於是前往曲平亭部投宿。確實漢代的亭有接待官員或百姓留宿之功能,但是在此處簡文中表達的是“曲平亭部”,亭部與亭不同點在於亭部是對亭轄區的稱謂,據王彥輝考證“鄉亭、郵亭的轄區稱‘亭部’”。[5]此外在五一簡中當出現亭部一詞時一般用作地名,如簡89中“縣民,占有廬舍長頼亭部”、簡432中“長、高等家皆在陽馬亭部”。因此此處趙壽移止曲平亭部,應當僅指趙壽所處的位置而無其他特殊的含義。最後來看該枚簡在整封文書中的位置,由於案件缺簡過多所以暫時不知該枚簡在整封文書中的具體位置,但是從簡文內容來看,其在這四枚簡中可能排在最後,簡文中初與壽的對話找中提到“卿來止出入一月”,則表明該枚簡敘述之事應當是案發後一個月或者是壽租賃初之籠一個月以後之事。而五一簡中解書的敘事順序一般按照時間來排列從前往後進行敘述,所以該枚簡應在這四枚簡中排在最後。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四枚簡在文書中的排列順序如下:
置初舍籠中,十月廿五日出之市,還,不知繒五十五匹所在,詣御門亭長丁壽,告壽收毄(繋)初。少Ⅰ名萇不處姓。萇辤:盜十五匹,不知餘所在。疑初與萇共盜壽,書到考實姦詐,正處言,則祉Ⅱ543(木兩行2010CWJ1③:261-23)
(缺簡)
貴汝何從得紙,貴曰:我於空籠中得之。初疑貴盜客物,即於壽比籠廋索,見壁後有繒物,初問貴是何等繒,貴曰不知,初曰:汝見持繒紙素言不知,即收縛貴,付661(木兩行2010CWJ1③:263-11)
(缺簡)
卿市繒當有主名。壽墨不應,明廿七日,趙壽與未央俱去初舍,不雇初籠僦直。初謂壽、未央:卿來止出入一月不當雇樵薪直?壽曰:我亡物,非能復謝卿。壽移止曲平亭部736(木兩行2010CWJ1③:263-86)
(缺簡)
兼左部賊捕掾則言,考男子范初
不與少、貴共盜趙壽繒,解書 詣左賊 £月□日開
2625+2553(木兩行2010CWJ1③:283-73+283-1)
(二)吳請、番當、番非盗發胡叔冢案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叁)》中有兩枚木牘似與一樁盜墓案件相關,《五一(陸)》公佈後又發現與這一盜墓案件相關的三枚簡,這使得該案件的案情逐漸清晰了起來。五枚簡中除一枚簡形製為竹簡外,其他四枚簡均屬於木兩行。為便於討論,暫將這五枚簡按照出版號順序羅列如下,標點為筆者所加:
六七尺不得冢戶,當、非曰:此冢殊深,非可得開,更復發他冢,請可,俱復發叔冢,冢去親家可卌餘步,請等掘深可四五尺,得延門當拔墼,請於冢上菅1057(木兩行2010CWJ1③: 264-211)
受生縳將詣亭。其月十五日,萌將請之弓、親、叔冢所,請辤:但發親、叔冢不發弓冢。到今月十二日,萌與叔俱之請所逃劒器,所溏水中得請所逃劒物1102(木兩行2010CWJ1③: 264-256)
見銅器,生疑發冢中物,請即持器去,出北索東行。時天雨,請辟雨怒門中,時生皆在門中辟雨,請解衣更浣濯,捉事已復衣,時生、怒見請銅器,怒問請若銅器寧賣1771+1775(木兩行2010CWJ1③:266-103+266-107)
廷移府記曰:男子吳請與番當、番非共發胡叔冢,盜取銅器。請捕得,當、非亡,家在廣成亭部,移書縣掩捕,考實有書,案非、當等所犯無狀,記到迺掩捕非、當。1774+2160+1758+2191(木兩行2010CWJ1③:266-492+266-90+282-3)
等逐捕考實盜發胡叔冢取銅器者吳請1791(竹簡2010CWJ1③:266-123)
由於涉及該案件的四枚木兩行形製相同,且文意相通,故首先來看這四枚簡是否屬於同一封文書,對於這一點一般通過判斷簡牘筆跡是否相同,是否為同一書手來進行認定。從簡文整體的書寫風格來看(見附錄),簡1057與簡1102應當屬於同一書手,而簡1771+1775與簡1774則並不確定其是否與1057、1102的書手相同,因此以下主要對比1771+1775、1774與1057、1102的書寫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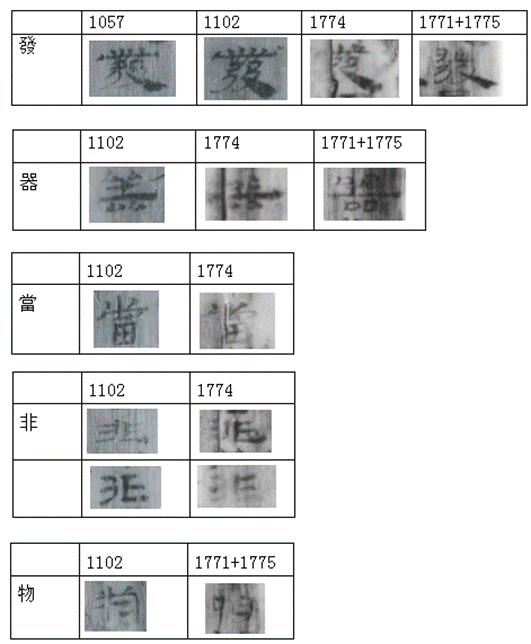
首先來看簡1774,該枚簡與簡1057、1102的書寫情況比較,主要通過“發”、“器”、“當”、“非”四字的筆跡進行對比。從“發”字的寫法來看,簡1057、1102所寫的“發”字上半部分是連在一起的,而簡1774雖然較為模糊,但是還是可以從中看出這一特征。在“器”字的寫法上簡1057、1102所寫“器”字的部首“口”的寫法呈現出三角形的特征,而仔細觀察簡1774的右下角“口”這一部首同樣有此特征。對“當”字而言,簡1102與簡1774在書寫風格上均整體的向右傾斜。最後來看“非”字的對比情況,從表中可以看出簡1102的書手在書寫此字時,並未將“非”字中間的兩筆“丨”貫穿整個字,而簡1774雖然較為模糊,但從殘存的筆跡上看依舊能觀察到此特征。因此綜上所述簡1774極有可能簡1057、1102屬於同一個書手。簡1771+1775與簡1057、1102的書寫情況比較,主要通過“發”、“器”、“物”三字的筆跡進行對比。在“發”字的寫法上,簡1771+1775與簡1057、1102有較大的不同,簡1771+1775的“發”字的上半部分明顯是分開的。“器”字的寫法,簡1771+1775與簡1102也同樣不太一致,簡1771+1775“器”字的“口”這一部首呈方形,而非簡1102中“器”字所呈現的三角形。最後在“物”字的書寫上,簡1771+1775與簡1102相差極大,不管是左部的“牛”旁還是右部的“勻”旁,均未見到相似的特征。綜上所述,簡1771+1775可能與簡1057、1102不屬於同一書手,而簡1774與簡1057、1102可能屬於同一書手。同一案件的文書中出現兩個書手,則說明這四枚簡牘可能分別屬於與案件相關的兩封不同的文書。因此暫將有着相同書手的簡1057、1102、1774定位文書一,將簡1771+1775確定為文書二。
在文書一中筆者認為簡1774可能排在首位。此枚簡以“廷移府記曰”曰作為開頭,“廷”應指臨湘縣廷,“府”指長沙太守府,而“記”則是一種文書形式,李均明認為“記”的功能與書、檄相同,但其體式更趨簡略。[6]而簡1774所屬的文書一,則屬於對府記的回復。在回復時需要將府記所述內容概括性的陳述一遍,在五一簡中這種陳述一般位於文書的開頭部分,如以下案例:
永初元年八月庚子朔廿一日庚申,廣成鄉有秩、佐种、助佐賜叩頭死罪敢言之。廷移府記曰:男子王石頭自言,女子溏貞以永元十四年中從石母列貸錢二萬,未選釋106(木兩行J1③:325-1-45)
廣成鄉印。
八月 日 郵人以來。
史 白開。選釋106(木兩行J1③:325-1-45)背
畢,比責,不肯雇。記到,實核,詭責。明分別正處言。种、賜叩頭死罪死罪。奉得記,即訊貞及石母列、知狀者男子鄭惠,辭皆曰:貞,□鄉民;列,都鄉,各有盧舍選釋54(木两行CWJ1③:325-2-3)
故簡1774在文書一所包含的三枚簡中應當排在首位。從簡1774對府記的概括陳述來看,這封府記要求下級抓捕與一樁盜墓案件的兩名犯罪嫌疑人“番當”與“番非”,該案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吳請”已經被抓獲。至於其如何被抓獲的,似乎能從簡1771+1775中看出端倪,雖然該枚簡並不屬於文書一。簡1771+1775中提到盜墓案的的犯罪嫌疑人“吳請”在拿著所盜的銅器時被名為“生”的人發現。而從屬於文書一的1102號簡可知,“吳請”正是被“生”抓住送往亭中。筆者推測正是因為此事才使得本案的調查得以啟動。一般來說在案件調查完畢後,需將調查結果呈交給上級,即簡1774中的“考實有書”,在調查結果經過上級的審核後,上級機構會給出意見,意見一般是令下級機構對案件某些不合理的部分重新進行調查[7],在下級機構重新調查後還需將文書呈交給上級,上級經過審核後若認為調查結果合理,便會請求長沙太守府下發逐捕文書[8]。
關於簡1057與1102由於案件缺簡太多,暫時無法確定其在文書中的具體位置,也並不能確定兩枚簡在文書中的先後位置。但是兩枚簡的簡文內容可相互印證,簡1102中犯罪嫌疑人“吳請”說自己之盜竊了親與叔的冢,並未盜竊“弓”之冢,簡1057也恰好是此事的一個還原,簡文中提到由於“親”冢太深無法挖開,故當、非、請三人“復發叔冢”。
作為一樁盜墓案件,本案對于研究東漢時期盜墓情況是很好的例證。目前學界對秦漢時期的盜墓情況研究多局限於秦時期以及漢代初期,主要因為這兩個時期均有關於盜墓情況的文獻出土。嶽麓秦簡中便有一樁記載盜墓案件的奏讞書[9],漢初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盜律》中也有關於盜墓案件是如何處罰的一則律令[10]。東漢時期的盜墓情況則由於缺乏傳世以及出土文獻導致研究較為困難。而五一簡中除本案之外還有一樁與盜墓相關案件,即簡426中所記載的“游徼張栩逐捕殺獨櫟例亭長、盜發冢者男子區義”一案,但由於五一簡並未完全公佈使得這一案件也同本案一樣缺簡過多,無法清晰還原案件情況。待五一簡完全公佈後,或許可以將這兩樁反應東漢時期盜墓案件的文書更為清晰的還原,這將為研究東漢時期的盜墓情況提供更為豐富的材料。
附錄:

[1]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伍)(陸),中西書局,2020年。下文均簡稱為《五一(伍)》、《五一(陸)》。
[2] 張朝陽:《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早期房屋租賃糾紛案例研究》,《史林》2019年第6期,第38頁。
[3]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年,73-74頁。
[4] 温玉冰:《朱宏、劉宮臧罪案復原研究》,簡帛網2020年06月09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557。)
[5] 王彥輝:《聚落與交通視閾下的秦漢亭製變遷》,《歷史研究》2017年第1期,第38頁。
[6] 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文物出版社2009 年,第111頁。
[7]429+430(木牘2010CWJ1③:202-4+202-5)“君教諾 左賊史式、兼史順、詳白,前部左部賊捕掾篤等考實南鄉丈田史黃宮、趣租史李宗毆男子鄧官狀。篤等書言,解如牒,又官復詣曹診右足上有毆創一所,廣袤五寸,不與解相應。守丞護、掾普議:解散略,請却。實核。白草”。該枚木牘即反映了由於下級機構在案件調查中出現差錯,上級要求重新調查一事。
[8]1509(木牘2010CWJ1③:265-255)“君教諾 兼左賊史順、助史詳白:前却北部賊捕掾綏等,考實男子由蒼傷由追狀,今綏等書言解如牒,守丞護、掾浩議,如綏等解平,請言府却逐捕。白草。”該枚木牘即是縣廷認為調查結果合理,決定請求長沙太守府下發逐捕文書的具體例證。
[9] 《嶽麓書院藏秦簡(叁)》案例三“猩、敞知盜分贓案”與“盜發冢”有關。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6月,第119頁。
[10]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66號簡“盜發冢,略賣人若已略未賣,橋(矯)相以爲吏,自以爲吏以盜,皆磔。”《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8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1年9月17日10:59。)